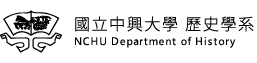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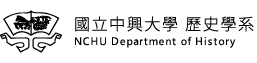
認識你自己──大家來寫村史與歷史意識的自覺
周樑楷
「大家來寫村史」的緣起
自從1970年代初期鄉土文學運動展開以來,台灣人民熱愛本土及其歷史的情懷,由隱晦轉而明顯,一天比一天地擴展。道了1998年,台灣大學歷史系吳密察教授「大家來寫村史計畫」強調從民間底層由下而上,不拘形式大家分別表述集體記憶或共同的歷史。這項計畫挑明了書寫歷史已不再屬於學院派內歷史學者的專利,同時地方史的呈現也不必受限於傳統方志的體例。
彰化縣政府及縣民頗能理解「大家來寫村史」的精神。在2003年年底,翁金珠縣長及文化局陳局長,規劃推展「大家來寫村史」,希望全縣每個村裡至少有本自己的歷史。縣長一再表示這項計畫的意義是:
今天我們終於可以讓我們的孩子解放出來,從自己的故鄉、自己的鄉土,認識自己的歷史。透過這種由微而顯的過程,才能真正形塑台灣集體歷史的記憶。
從那個時候起,陳利成、林琮盛、陳板、康原和我應邀成立委員會,積極推動村史撰寫計畫的各項業務。每月聚會一次與各村史的撰寫者面對面討論如何收集史料、考訂真偽、去蕪存菁以及撰述寫作。後來,也敬邀吳晟和宋澤萊兩位先生參與評審。回顧這一年來的過程,我們首先從近四十篇的研究計畫中挑選了十九篇,接著每位撰寫者按計畫進行,而後完成寫作,通過審查、得予出版者共有十篇。由此可見,現在呈現在眾人面前的十本村史,都是計畫撰寫者竭盡心力的結晶,也是經過精挑細選,獲得肯定的成果。
彰化縣推展「大家來寫村史」是種永續經營的志業。這種運動首開全國風氣之先,並且以「大家來寫村史」結合「社區總體營造」和「鄉土教育」,期盼人人寫村史、村村有歷史。這個年度的工作成果只能算是整個運動的「暖身」而已,緊接著從2005年起,將全面全速進行。彰化縣民邁步向前,走在時代的先鋒。「大家來寫村史」是來自底層的歷史意識和在地意識,更重要的,是民間的自覺運動。
大家是誰呢?
「大家來寫村史」的「大家」是指哪些人呢?
什麼人才有資格書寫歷史呢?中國上古時代所謂的「史官」,身分屬於貴族,而且可以世襲。記載歷史,美其名是他們的天職,說穿了就是他們的特權罷了。底層庶民不識文字,既不懂得書寫,官方也不准許私人著述。他們頂多只能以言語、歌謠或各種圖像表述他們的記憶和歷史。兩漢以來,先是世家大族,而後是宦官文人,由於位居知識階層才能有能耐以文字撰述。眾多的百姓一直與歷史絕緣;他們無能書寫歷史,更何況史書也疏少記錄他們。所謂的「正史」,那是種經過皇權認可的紀傳體作品。而所謂的「方志」,是種地方官僚體系及鄉紳運作出來的記錄,作為官方統治民間的參考書而已。
古代西方世界的情況與中國大同小異,書寫歷史總是屬於少數人的特權。不過,西元前六世紀的雅典曾經有次重要的突破,值得我們現代人省思和效法。上古時代雅典和希臘個城邦一樣,政治上都屬於貴族政治,思想觀念上則以神話的方式思維周遭所有的問題。雅典北部德爾菲(即Delphi)的阿波羅(Apollo)神廟,門楣上銘刻著:「認識你自己」(Know Thyself)一行字。原意是說,來此問神就可以得知你的吉凶和命運了。
當時人們有任何的疑惑祈求神明的指引,都到廟前請示神諭(oracle)。不過,值得留意的是,詮釋神論的工作屬於祭司的專利,或者更正確地說,詮釋權屬於統治階層的貴族,因為當時祭司一言一行還得觀察貴族的臉色。十八世紀義大利的思想家維柯(Giambatitista Vico,1668-1744)在其著作《新科學》(New Science)中指出:
[雅典]的英雄,同時也就是貴族,宣稱自己擁有神的血緣。由於這種天賦本性,他們說諸神屬於他們的,同時以因此占卜問神的權力也屬於他們。
然而到了西元前594年,梭倫(Solon)擔任雅典的執政官,他一心一意促進雅典政治的民主化,採取不少改革措策,因此贏得不朽的美譽。這個時期,整個希臘的思想文化也日漸進步,邁向理性,重視科學。例如,泰利斯(Thales,ca.624-554B.C.)和安那克曼德(Anaximandes,ca.611-574B.C.)等思想家大約都生長在這個時代裡。通常我們所閱讀的希臘史都會刻劃雅典民主政治的發展以及希臘思想的革新。不過,這些作品幾乎都將這兩大事件分別描寫,好像風馬牛不相及一般。維柯在《新科學》中卻特別強調:梭倫轉化了「認識你自己」這句名言;梭倫告誡平民百姓都應運用自己的理性思維,決定自己的所作所為,而不是完全迷信神諭以及祭司或他人。由此可見,梭倫的貢獻在於同時促進了雅典政治的民主化和思想的平等化。
維柯將政治社會史與知識思想史結合起來是項重要的貢獻。他的觀點不僅可以用來說明近兩百年世界各地的史學史,而且也可以解釋台灣近幾十年來歷史意識的覺醒。
自西元十九世紀以來,西方世界的大學裡紛紛成立歷史系,以便培養專業史家(professional historian)。這些由學院派養成的學者,畢業後分別佔據研究院、大學和中學,從事研究及教學的工作。他們雖然取代了過去具有官方身分或文人階層的業餘史家(英文通稱為amateur historian)不過,相對來說仍然屬於社會上的少數人。尤其這些專業史家往往偏重菁英主意,主顧由上往下觀看歷史,忽略一般常民的生活和文化。他們所書寫的歷史,由於一向標榜理性,遵守嚴謹平實的風格,難免矯枉過正,反而失之於刻板,不夠生動活潑,難以卒讀。此外,近兩百年來的專業史家多半受國家主義或民族主義(nationalism)的影響。他們有意或無異間奉國史論史(national-history discourse)為正典(canon),因而輕忽地方史、弱勢族群,以及各種「他者」(the other)的歷史。其中比較嚴重的實例,有如薩伊德(Edward Said)在《文化與抵抗》(Culture and Resistance)裡一篇訪談中所指出的:
[新一代以色列歷史學家]耙梳各種歷史資料及檔案文件,重新檢視了以色列的國族論述,發現他[以色列]的獨立和解放神話是奠基於對阿拉伯人存在的否定,或擦拭,或頑固的迴避。
近二十幾年來。全世界的政治潮流比從前更加民主化,同時思想文化也更朝向平等化,各弱勢族群逐漸取得自主發生的權利。台灣在這兩股潮流中,表現亮麗,不落人後。如果以古希臘梭倫轉化「認識你自己」這句名言的道理,我們再度將之轉化和深化時,可以說成,在今天這個時代裡,「認識你自己」應屬於每個人的權利,換句話說,人人都有表述歷史的權利,人人都是史家。所以「大家來寫歷史」的「大家」是指社會上每個個人。為了提倡「大眾史學」,我曾經位「大眾史學」下定義:
每個人隨著認知能力的成長都有基本的歷史意識。在不同的社會文化中,人人可能以不同的形式和觀點表述私領域或公領域的歷史。大眾史學一方面以同情了解的心態,肯定每個人的歷史表述;另方面也鼓勵人人「書寫」歷史,並且「書寫」大眾的歷史,供給社會大眾月聽。大眾史學當然也應該發展專屬的學術及文化批評的知識體系。
2004年度參與彰化縣村史計畫的撰寫者都由內而發,表示書寫村史是他(她)們的權利和職責。例如,《瑚璉草根永靖心》的作者邱美都說:
我認為在地人有權利和義務,詮釋自己村莊的常民生活史,當下選擇撰寫我成長的永靖鄉瑚璉村。我以歷史發展為主軸,以村民共同的生活記憶為肢幹,融合史料、口述歷史、田野調查、在地經驗、圖像等營養素,以報導文尋方式,期望能架構一本有跟有枝葉的書,一本有骨架又有血肉的瑚璉村莊史來。
又如,《油車穴傳奇》的作者巫仁和說:
對家鄉土地與人們的關愛,是本能的,因為我出生在這裡,成長在這裡。從古老的年代開始,這塊泥土便育養著無限多的生命,它們與人們的生命都有著關連;像我的生命歷程中,便受到無數親族鄰友的照顧和鼓勵,家鄉的每個人都有著密切的關聯。
彰化縣文化局為了促進「大家來寫村史」運動,沒有訂立任何門檻或資格限制,原則上任何縣民都可以提出研究計畫申請書,甚至已經外出、移居其他縣市或國家的「彰化人」也都可以參加。至於我們這幾位所謂的諮詢委員,只是負責審查計畫申請書的可行性以及輔導研究撰寫的工作而已。
書寫哪裡的村史呢?
既然「認識你自己」屬於每個人的權利,也是「大家來寫村史」的理論依據,於是我們可以進一步直言,在地人都有書寫自己的權利、在地人都有書寫在地歷史的權利。人們如果打從心裡懂得這點道理,其實就是歷史意識和在地意識的覺醒。接著,我們要追問,在地人應該書寫哪裡的「在地史」或「村史」呢?
按古拉丁文的原意,indigenae指「本地出生的人」由這個名詞衍生出「在地人」的意思。由於在地人熟悉在地的人、事、物,舉凡一草一木都耳熟能詳,所以在地人最能享有一切,進而對在地感覺滿足和喜愛。因為在地人偏愛在地的一切,覺得在地的一切樣樣順心如意,有特色,比外地的更好,所以古拉丁文indigenae最初也含有「高貴的」意思。這種感覺就是我們今天所謂「在地意識」、「本土意識」或「鄉土意識」的源頭,相當於英文的indigenity或parochialism。
「在地」或「村里」當然指某個「空間」(space)。然而「空間」是個中性的概念,只有小大之別,沒有任何主觀的含意,所以僅僅使用「空間」的概念來思考「在地」或「村里」是不夠的。「在地」或「村里」應該指某個「地方」(place)。在英文裡,place含有社會、文化,甚至歷史等主觀的因素。所以,place也可以是position(地位)。「地位」是主觀上的評價,當然最好能名副其實,配合實際客觀的狀況。Place用在地理空間上,應該是漢語裡所說的「地方」。「地方」不僅有大小之別,而且隨著歷史及時間變遷,以繁榮、蕭條、開展、封閉等痛景象,與周遭各「地方」的相對關係,時而處於核心位置,時而淪為邊陲。當我們採用place指「地方」、「在地」或「村里」時,最好應該掌握以下三項因素:
n 它是能自成最小單元的地方。在英文裡,中古時代的parish,指一個個的「教區」,有點類似台灣早期漢人社會中所說的「祭祀文化圈」。教區的「區」,或文化圈的「圈」,就是最小單元的「地方」,也是現代英文中所說的parochial。台灣人所說的「庄頭」、「村莊」,或原住民所說的「部落」,勉強類比的話,較接近西方中古時代的「莊園」(manor),也都個自成最小的社會單元,是最基本的local。
n 它結合在地文化、社會與自然為一體,形成具有特色的生活文化圈。人們朝朝暮暮生活在期間,自然而然地產生認同感,形成所謂的鄉土意識、本土意識(parochialism)或地方主義、地域主義(localism)。
n 它隨著時間和歷史而變遷。文化、社會和自然都是動態的,每個「地方」的改變只有快慢緩急的差別而已,累積為小的「量變」到了一定時候可以釀成「質變」,滄海成為桑田,小地方成為大的市鎮,農業社會成為工商業社會。生活在期間的不只有個人記憶和集體記憶,而且進一步有變遷的意識(the sense of change)。懂得以變遷的意識思維,掌握過去、現在和未來的互動關係,就是能以歷史思維(historical thinking)辨別事物的人,通稱為具有歷史意識(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彰化縣民「大家來寫村史」運動所說的「村史」,其實只是個代用的名詞,圖個方便而已。「村」指的就是具有上述三項要素的place(地方、在地、村里);而「村史」就是這些「地方」的歷史,又稱為最小單位的「地方史」。彰化縣文化局期盼「村村有歷史」,意思是指每個「地方」都有本「地方史」。這些「地方」,我們切忌以現行地方行政單位的村、里或鄉鎮為單位,而是具有彈性的,甚至可以比村、里的範圍更小,只要掌握上述三項要素就不離題了。同時,彰化縣文化局也鼓勵「人人寫村史」,意思是說每個人都有權利以自己的角度、視野(perspective)撰寫歷史,所以每個「地方」並不限於僅寫一本「村史」而已。「大家來寫村史」如果順利展開,其實是種社會運動,也是種文化運動。
怎樣「書寫」村史呢?
村史應該長什麼模樣?怎樣書寫呢?
任何歷史作品的生產過程,從無中生有,不外乎兩大步驟:一是史料的蒐集和研究;另一是史書的撰寫。針對這兩個步驟,我曾經為「歷史」下定義說,歷史ˋ對於過去事實的認知極其傳達的成果。這個定義的前半句話,涉及史料的蒐集和研究,後半句指的就是史書的撰寫。
假使我們把史料彙編成冊,離供他人使用,這是功德無量,很有貢獻。清代史家章學誠在《文史通義》里稱呼這類作品為「記注」。至於作者根據史料進一步加以歷史解釋(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然後表述(represent)出來,其成果就是史書了(指廣義的)。章學誠說這類作品為「撰述」。
史料的蒐集以及研究貴在豐富和嚴謹。史料的數量永遠不嫌多,越豐富、越多元就越好,只是應該嚴謹處理,加以考證排比。章學誠把這層能耐比喻成「蕭何轉餉」。三軍作戰,後勤人員負責轉運糧食軍備,不僅要定量,而且要及時抵達,這需要周密的規劃,以及辛勤的執行,所以又簡稱為「方以智」。
史書的撰寫必須以自圓其說的歷史解釋,駕馭所有的史料,使得史觀主題十分清晰。章學誠把這層功夫形容為「韓信用兵」。主帥指揮三軍,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所以又簡稱為「圓而神」。
轉寫村史的步驟和理想離不開「蕭何轉餉」和「韓信用兵」。踏入村史的第一步最苦惱的莫非巧婦難為無米之炊,茫茫然不知史料在哪裡?推測其因,這多怪一般的史書,包括地方志在內,往往研究得不夠細膩或忽略底層常民。例如,《甦醒中的王功》的作者魏金絨說:
曾參與鄉、鎮志的編寫,發現寫地方是件難事;因為相關的史料很貧乏,察考困難;鄉野訪談所得,常有所偏,內容無法盡信;如果要求完美,就必須廣泛蒐集,大膽推敲才有所成。如今縮小範圍寫村史,又出現相同的問題,而困難度則有過之。
「大家來寫村史」運動的諮詢委員為了指引迷津,協助計畫撰寫者蒐集史料,每次都利用聚會時間,以個案處理的方式,盡量提供參考意見。我們都認為「從做中學」是最佳的途徑。在此僅能提出幾個原則:
n 史料是多樣的,必須主動出擊。
n 文字的史料:鼓勵村民大家獻寶,每家的抽屜裡各類的文獻、筆記、收據……都可以。
n 語音的史料:以口述歷史的方式訪談,讓每位不善於提筆的也有發聲、表述歷史的權利。
n 圖像的史料:不會自己說話的對象,例如:建築、文物、河川、一草一木等,可以照片或速寫記實。最好是每本村始終都有幾幅自己繪製的「文化地圖」,按照不同的時代呈現出來。
「從做中學」之後,所得的甘苦經驗往往最甜美、回味無窮。邱美都回憶說:
緊鑼密鼓的訪談和田野調查,也許是艱鉅任務,對於瑚璉村而言卻是史無前例,不過村民支持、期待,也願意分享,於是週末假日,四處拜訪瑚璉的阿公阿嬤和鄉親,聆聽他們的生活故事,一位接著一位訪談,一處接著一處踏察,很快就成為朋友。外子銘欽耐心地隨同攝影,回家立刻在電腦上記錄或對比資料,經常是入夜還無法罷手,我的三個孩子很獨立,也都成為小助手。有時將採訪的故事說給孩子或學生聽,沒想到年輕的一代比誰都愛聽,因為許多生活故事,在學校往往無法深入觸及。一年下來,有酸有甜有甘有苦,與其說是犧牲假日的休閒生活,不如說這是最有意義的另類的休閒方式。
史料固然可貴,然而「大家來寫村史」運動的理想,是完成「寫給大眾喜歡閱讀的歷史」,所以我們有「三不原則」:(1)不要史料彙編的作品;(2)不要類似台灣各地方行政體系近期出版的「地方志」;(3)不要學院派的專著。一般人書寫「地方志」及「村史」最容易觸犯的毛病,是未能區別「記注」和「撰述」有何差別,結果混淆在一起不倫不類。章學誠強調說,「記注」和「撰述」之間,「合之則兩傷」,「離之則雙美」。我們希望大家所書寫的村史屬於圓而神的撰述,讓大家喜歡,或者給學童當作鄉土史的教材。就此而言,理論上村史的表述應該多元而且多樣,凡是文字、語音、圖像、展演等無所不可。吳密察教授當年所推動的計畫以是朝著這個目標。不過,萬事起頭難,彰化縣文化局現階段所發動的「大家來寫村史」,策略上穩紮穩打,僅提倡「以類似報導文學的文體,配合多種圖像(如照片、圖畫、表格、文化地圖),綜合表述」。這種表述的體力達成一定的水準後,我們或許可再進而提倡其他體例的村史。
就整體而言,村史應該呈現常民的生活文化圈。我們不希望只記載地方長官以及富貴人家而已。村史的撰寫者因為生於此、長於此,與在地人的距離比較「黏」,所以個人的好惡往往主觀鮮明。每位撰寫者應當小心切忌阿諛、鄉愿。再說,除了人物和家族外,應多描述本地昔日特殊的習俗、事件、諺語、傳說、古地名、自然環境、動植物等等。面對自己成長的家園和村裡,除了記載正面的「開發史」、「發展史」外,不妨多寫點昔日常民的辛酸血淚、挫折奮鬥過程。村史撰寫者熱愛鄉土之餘,何妨愛之深、責之切,對地方的整體發展寫點善意的批評以及對未來的展望?
村史運動的展望
彰化縣文化局領先全國各地,於2004年首度推展「大家來寫村史」計畫,同時為了提昇縣民的興趣及研究的能力,在十一月間委託逢甲大學歷史與文物管理研究所舉辦「大家來寫村史研習會」,我有幸同時參加兩項工作。
「大家來寫村史」是永續經營的志業,而且最終是縣民們大家自動自發,由下而上的運動,我們希望「人人寫村史」、「村村有歷史」。透過這項運動累積的成品,首先可以促進歷史意識和在地意識的結合與發展,其次可以使得村史運動與鄉土教育相輔相成,密切結合,發揮最大的效果,最後形成由下而上的自覺運動,由最小單元的村、里或地方將全縣連結在一起,並由此影響全國的文化取向。
註:本文引自,台北市立教育大學,《2008美術與人文教育通識教育研討會論文集》。台北,2008年。作者:周樑楷,逢甲大學歷史與文物管理研究所教授。